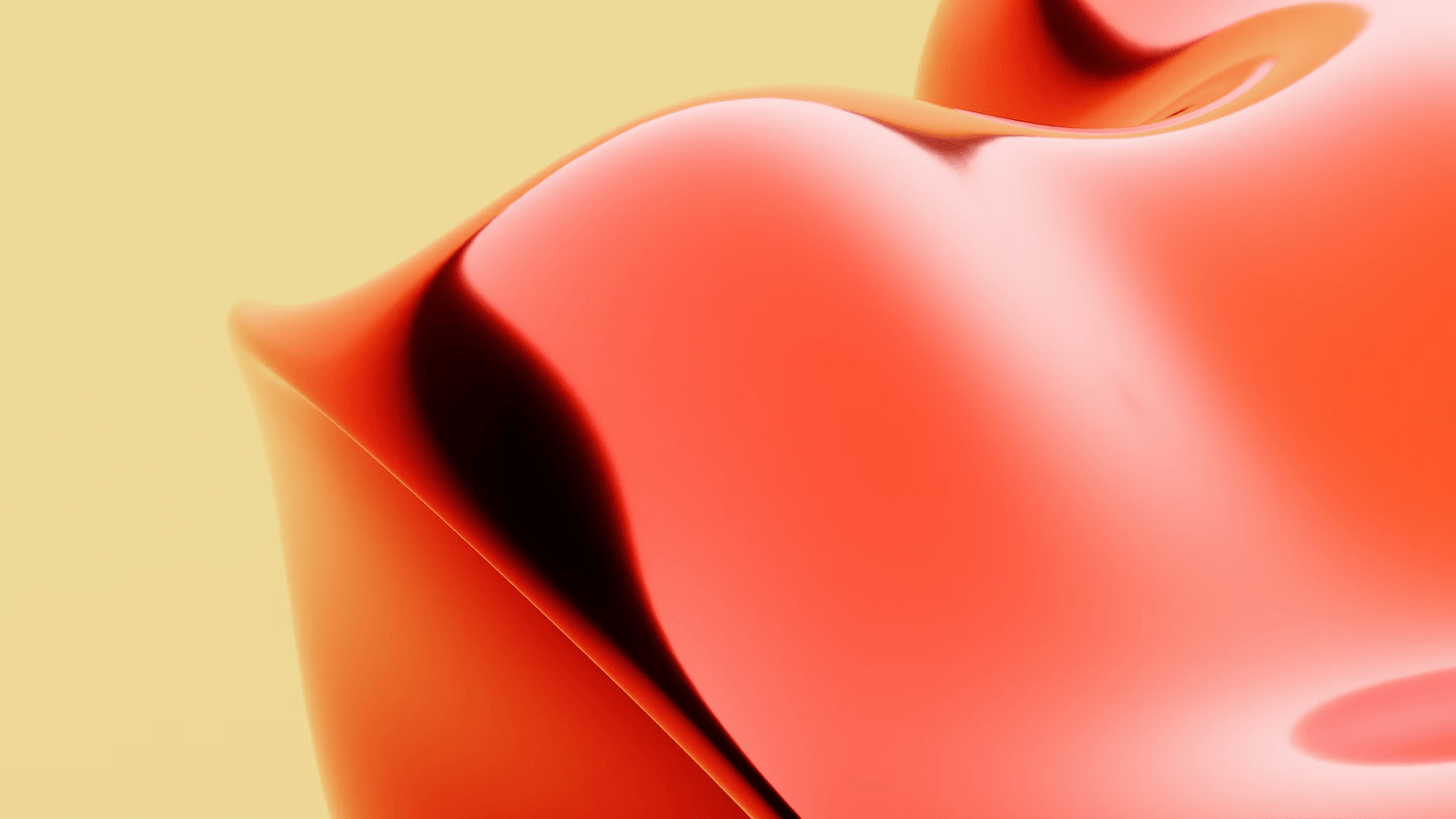
「還願」的政治解讀(文長,劇透。) https://www.facebook.com/mock.mayson
前陣子「還願」的赤燭團隊重新架設了自己的平台販售遊戲,週末期間我也把「還願」再重新玩了一遍,順便把放在心裡很久的遊戲感想寫出來跟大家分享。
—————-
一、成長於蔣經國時期的杜美心
如果說「返校」中的方芮欣學姊是成長於蔣介石時代,那麼「還願」中的杜美心妹妹就是成長於蔣經國時代。
杜美心的出生年份被設定為1975年,也就是蔣介石身亡的那一年。大約在蔣介石死亡三個多月之後,杜美心就出生了(7月27日)。而杜美心死亡的日期是1987年10月7日,她死後三個多月,也就是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也接著七孔流血暴斃身亡了。
換句話說,杜美心的一輩子基本上就是活在蔣經國的主政統治之下。她的人生短短十二年光陰幾乎都是活在中華民國軍事戒嚴的狀態之下,只有餘生最後的84天(兩個多月)才是活在解嚴的時期。然而這朵黃色小花還來不及長大目睹野百合盛開的台灣民主浪潮,就死於戰後嬰兒潮出生的杜豐于手上。(玩家也有另外一派的解讀,認為杜美心並沒有死,死的是父親杜豐于,劇中的男主角杜豐于其實已是亡魂,需要被女兒杜美心超渡。)
杜美心的成長期間,台灣社會剛好也發生了數件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包括中壢事件、高雄橋頭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楊清化血案、陳文成遭國民黨特務殺害事件、江南案等,卻因為所有的大眾傳媒均被中國國民黨給控制封鎖,所以一般人其實很難理解這些事件的嚴重性,甚至還會被國民黨提供的假新聞給誤導。
蔣經國因為少時背景而深諳共產黨的兩面統治手法。一方面以暗殺、血洗與整肅的方式來對付想要爭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另一方面,又試圖以操控媒體的方式來左右大眾視聽。蔣經國不但佯裝成吃路邊攤然後到處long stay的可愛小胖子,還鼓勵放送單位用大量情歌與校園民歌以及歌唱選秀(五燈獎)的方式來粉飾太平與麻醉大眾,並且要求政府單位查禁具有反抗權威意識的歌曲。
杜美心等一家人當然也不可能從那台被黨國控制言論的電視上得到任何資訊或是啟發。「還願」的客廳場景中一直出現那台只剩白噪音訊號的電視,其實對我來說就像是在反諷那些從小沉溺在黨國老三台電視而至今仍不清醒的蒙昧民眾。看看那些整天只會看中天TVBS的韓粉飯統,其實跟發瘋後(死後)只會坐在客廳呆看白噪音電視的杜豐于沒有兩樣。
—————-
二、治安破敗的戒嚴時期
你在「還願」的場景中可以看到一堆鐵門鐵窗,你有想過這些鐵門鐵窗是怎麼來的嗎。讓我們先來看看那個曾經參與倒扁紅衫軍也最痛恨民進黨的羅大佑是怎麼在專訪中形容那個「治安良好的戒嚴時代」:
******
1983年的某個午後,羅大佑和張艾嘉在台北市永康街吃牛肉麵,旁邊一桌的年輕人經過的時候問:「欸?妳是不是張艾嘉?」張艾嘉回說:「是啊。」對方立刻大笑跟旁邊的朋友說:「你看!她就是啊!」原來這群人是在打賭,賭輸的老大不服氣地發火,對羅大佑嗆聲:「你害我輸!不讓你走!看你要怎麼辦!」這群沒事找碴的人就這麼和羅大佑糾纏了半個鐘頭。
還有一次是羅大佑還沒出道前,開車到民生社區找女友,在一個路口要轉彎時對向剛好有來車,他停在中間讓對方先過,沒想到駕駛下車衝過來怒罵:「你要怎樣?想打架嗎?」還作勢毆人。羅大佑說:「我是好意停車讓他先走,但他會把這當作挑釁,那個年代的氣氛是這個樣子,在街上看誰不順眼,隨時會動刀動槍的,跟早期的體制有關係嘛,大家都武裝起來,很具攻擊性,報紙上寫的暴力亂象都是真的。」
******
(上文引用自蕭卲樺於2017年採訪羅大佑的文章)
對,國民黨支持者最懷念的戒嚴時代就像羅大佑所說的「大家都武裝起來,很具攻擊性,報紙上寫的暴力亂象都是真的。」羅大佑自己受訪都說他當年離開台灣的原因就是因為戒嚴時期的治安實在太糟。
你現在在路上看到那些沒水準、缺乏公德、邏輯敗壞、做事馬虎、迷信胡言甚至還有暴力攻擊傾向的中老年人就是戰後中國體制教出來的一群無良產物。本來他們還是細漢的時候還有日治時期成長的家長在管教著他們,等這些日治時期的大人們走光了,這群中國時期長大的華腦老屁孩才正要以各種方式危害台灣。
排隊?戒嚴時代沒有這種事情。你現在在商場或是超商看到一堆喜歡插隊或是在你還沒結帳完就急著把商品拿到櫃臺前的中老年人,就是在中華民國戒嚴時代活得毫無尊嚴也完全不尊重自己的生物。
那些年他們上市立聯營公車跟台鐵火車的時候搶成一團,到福利社跟柑仔店買東西的時候搶成一團,在菜市場跟診所掛號的時候搶成一團,開車騎車在路上也是酒駕闖紅燈爭搶道搶成一團。我小時候對這些中華民國教育教出來的爛人樣貌記得一清二楚。長大之後這些很雷的老人跟當年一樣狗改不了吃屎,只是多了些皺紋跟白髮,然後跑去支持國民黨跟韓國瑜而已。
黑道、雛妓、綁票、殺人、竊盜、搶銀行、警察索賄、飆車族砍人、少年隊揍人,這些正是中華民國戒嚴時期甚至到解嚴初期都可以看到的日常風景。中國製的紅星跟黑星手槍到處都是,一把只要兩萬五千元台幣就可以買到,道上兄弟幾乎人手一把。
「撿到槍」在當代的意思是指直言不諱或是發飆開罵。但是在中華民國戒嚴時期的八零年代,「撿到槍」的意思就是真的撿到槍,Literally。當時的國民黨內政部長許水德在面對質詢時曾說「這幾天我們走路真的會撿到槍。」(1989年10月24日,該年度從一月到七月為止已發生高達九十幾件的綁票案,被槍殺者四十多人。)你到一些公廁、工地或是廢棄空間,還有很大的機會發現強力膠、速賜康、紅中、白板、青發的用後殘跡。(這就是上一代的華國老人在嗑的東西。)
回到「還願」的場景,台灣為什麼會在戰後出現全世界最醜的鐵窗鐵門景像,每家的窗戶都裝上監獄般的鐵窗,就是因為嚴刑峻法的戒嚴時期根本無助於消滅犯罪,中華民國戒嚴時代反而是台灣史上治安最敗壞的時期。
連在1981年到1984年期間擔任內政部長的林洋港都在戒嚴時期說過這樣的名言:「三個月內要讓鐵窗業蕭條。」結果哩?什麼屁都做不到,治安更是糟糕,竊盜更是興盛,鐵窗業更加興盛。那些說戒嚴時期治安很好的人,不是整天看老三台黨國新聞還信以為真的蠢蛋北七就是睜眼說瞎話的黨國打手。
—————-
三、破敗髒亂的中華空間
你在「還願」遊戲中看到破敗骯髒的居住環境,貼滿亂七八糟小廣告的樓梯廊道,一堆缺乏公德心的人把公共通道堆滿自家雜物垃圾,還因建商偷工減料而漏水斑駁還到處壁癌的黑暗空間,就是一群中華民國人所懷念的中華黨國戒嚴時期的真實生活樣態,也是台灣人被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後所必定會產生的難民空間。(現在很多地方還是如此。)
連許多外國玩家在玩「還願」的時候都在問說怎麼那麼髒,應該要有人來打掃一下吧。但是對大多數有點年紀的台灣人而言,當時這種糟糕的環境的確是不陌生也不意外。日本時代那個愛乾淨的台灣人早已逝去,中(華民)國統治四十年(「還願」的設定年代),倒是教育出一堆缺乏公德心的台灣人。
我跟杜美心差不多是同輩,從小生長在台北市,也經歷過戒嚴時期。她小時候所經歷的環境與時空,我大概也都經歷過。所以當我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特別有既視感與同理感。影像與空間記憶力算是不錯的我,小時候依舊記得非常清楚戒嚴時期整個敗壞空間的狀態。
小學時候因為身高還沒長高,比大人的視角更能貼近地面,所以你會非常清楚看到戒嚴時期的80年代台北其實是滿地的菸屁股、口香糖、檳榔渣血、紙屑垃圾、還有到處可見的黃痰、嘔吐物與狗大便的噁爛狀態。
在公寓的樓梯間你會看到搬家公司用鏤空模板噴上一堆很難清除掉的噴漆廣告,在馬路上你會看到一堆沒有用安全圍籬圍起來的磚塊、鋼筋與建築用砂土,在人行道上你會看到因為施工不良而破裂缺角的紫紅色路磚。在台電水泥電線杆的孔洞裡你會看到一堆菸屁股、吸管跟垃圾。在大排水溝裡你會看到一堆響應國民黨「家庭即工廠」(住商工廠不分區)政策的小型工廠排出的噁爛黑渣與化學物。
我小時候還會撿起路邊的石頭,瞄準排水溝中流動的噁心黑渣投擲。鄰居的耆老會跟你說排水溝以前有著滿滿的大肚魚跟蝌蚪,在我成長的戒嚴年代已經看不到這些生物了。所以認為國民黨會在乎環保、空汙或藻礁議題甚至跟國民黨結盟連署環保議題的人根本北七無誤。
然後你會看到每戶人家幾乎都會使用工廠才會使用的慘白日光燈管來做為居家照明。如果日光燈管開始故障閃爍,整個居家空間就會弄得像女鬼鞏俐芳快要出現的樣子。難怪一堆外國人來到台灣都會問說為什麼台灣人喜歡把自己的居家照明弄得像工廠一樣,一點溫暖的感覺都沒有。
這就是張哲X跟一堆九點二所懷念的中華民國戒嚴時期的生活空間。一整批被中華民國教育教出來的「中國人」世代住在像病死豬住的髒臭環境裡面,還開心得不得了哩,只整天想著發大財撈一票後就趕快移民到乾淨的國度,而從來不想要把自己居住的空間給弄乾淨。
「還願」的空間重現只是剛好讓玩遊戲的年輕世代可以體驗一下你們上一個世代在戒嚴時代所成長的「豬窩」是長什麼樣子而已。
—————-
四、杜美心的類北京腔調
在「還願」的「七彩星舞台」電視選秀節目中,你可以聽到杜美心用一種仿北京腔咬字的方式在唱「碼頭姑娘」,尤其是ㄓ、ㄔ、ㄕ的發音在捲舌時特別地用力與怪異,也算是重現戒嚴時期廣電節目中總是會聽到的類北京口音,足見製作團隊在考究上的用心。
基本上這種混合了王炳忠、視網膜外加洪秀柱的奇怪腔調就是中華民國戒嚴時代的變體北京腔發音。當時你打開電視,除了只准在中午時段播放的台語節目之外,聽到的全部都是這種類北京腔的怪音調,也就是所謂的「標準國語」。
講到「標準國語」就不得不講到蔣經國。深諳語言就等同政治的蔣經國曾在一九七三年為了消滅台語,將老三台收視率超高的台語劇全部停播。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文工會甚至還要求「國語連續劇」要講「標準國語」,也就是說講北京話還不夠,還要講字正腔圓的標準北京話。杜美心過度矯正咬字的類北京腔調就是來自於此。
蔣經國的劣行導致一堆台語演員被迫要在攝影機前講北京話,結果這些母語非華語的演員講得痛苦,觀眾也看得很痛苦,後來編劇乾脆把有台語演員的戲劇全部改成悲劇,因為悲劇就可以慢慢地講台詞,台語演員才可以像林洋港一樣慢慢地咬文嚼字,跟杜美心一樣努力地把ㄓ、ㄔ、ㄕ給念清楚。
若台語演員還是沒辦法講「標準國語」呢,那就讓他們講「台灣國語」。電視編劇們就把劇情改成喜劇,讓這些講「台灣狗語」的演員變成丑角。例如台視的首部「狗語」連續劇「台北人家」,飾演在「高級外省人家」幫傭的下女「阿桃」,就是這樣一個操著「台灣狗語」的角色,在劇中專門用來鬧笑話給滯台中國人哈哈大笑的低賤工具人。(上三段文請參見管仁健的「外省新頭殼」一書,頁75-78)
「高級中國人」看待「阿桃」的方式就是他們看待台灣人的方式。「阿桃」若是真的硬要在「北京話」的時段講台語的話,那麼這些國民黨人會怎麼處理呢?管仁健曾經整理過中華民國戒嚴時代由「高級中國人」制訂出的「台語使用三要件」潛規則:
一是要用粗話罵人時。
二是代表說話人是反派時。
三是形容很苦、很窮、很倒楣時。(「阿桃」就是這樣的人設)
這就是很多戒嚴時期成長的中老年人會瞧不起說台語的人的重要原因。很多台灣人就算自己家庭的原生母語是台語,也恥於在公開場合說台語,甚至看到說華語的人還要勉強自己說華語,根本就是一付被完全殖民的奴顏樣。
中國人的母語歧視政策也導致許多台語家庭出生的年輕人,因為大眾傳媒的華國歧視而恥於在公共場所開口說自己的母語,甚至還會刻意矯正自己的口音(老一輩就屬林洋港與侯友宜是最為人知的例子)。這種情況也同樣可見於客語族群以及原住民族群。
香港現在也步上台灣被中國殖民的後塵,大概只要一到兩個世代的時間,你就聽不到現在的香港人講香港話,香港將來也會跟台灣一樣,只剩滿滿的北京矯正腔與對母語的自我厭惡感與貶低感。諷刺的是,被英國統治一百多年,香港仍然保有自己的母語香港話,同樣地,被日本統治五十年,台灣人依舊說得一口流利台語與客語,但是只要被中國殖民個半世紀,保證你的母語與歷史記憶被消滅得一乾二淨。
台灣一直要等到解嚴之後,這種怪腔怪調的類北京發音才開始逐漸在電視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才是比較接近正常台灣人說話的腔調或是全台語的節目與廣告。(民進黨執政時還成立了「客語台」、「原民台」、「台語台」。)但是「台語使用三要件」的潛規則卻依舊在解嚴後於各類廣電節目中延續了許多年,至今也還沒有消退的跡象,即使是公共電視製播的電視劇都還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許多天龍人跟華語族群也只有在講髒話的時候才會使用台語或客語,除了顯示這些人根本無法理解台語與客語的優雅與複雜層次的表現用法,也透露出這些人下意識將台語客語視為卑賤下人的語言而予以調侃,嘴巴喊著反歧視的時尚口號,自己卻整天在做歧視自己母語的事情,所以前陣子才會鬧出黑素斯與薔薔的三洨事件,而這絕對不會是最後一件因為有意或無意間貶低台語而造成台灣人反感的事件。
—————-
五、漫畫審查制度下的「花與愛」
基本上,杜美心在中華民國軍事戒嚴的狀態下,不大可能看到像是「花與愛」這種台灣自創的童話繪本。
因為在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就制訂了「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用愚蠢的華腦角度審查所有的漫畫或是插畫作品,導致一堆具有原創性與發展商機的台灣漫畫紛紛遭到腰斬停刊,出版台灣本土漫畫的出版社也因此被迫倒閉,最後也導致了中華民國盜版漫畫的氾濫、台灣漫畫人才的世代斷層與民眾普遍想像力與創意薄弱等問題。
當時國民黨制訂出的「連環圖畫審查標準」中有一項條文明訂:「超乎人情事理以外的神怪故事及以神力解釋自然的神話故事,己不合時代需要,又易使人思想誤入歧途,一律不准創作。」
「花與愛」繪本裡面提到的「豐饒神」、「幫小女孩搭橋的胖胖熊」、「會說話的大仙鳥」基本上一定會被中華民國政府根據「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判定為怪力亂神而打槍劣退。杜美心當時可以看的神怪繪本大概只剩下「西遊記」跟「聊齋誌異」。想看點不一樣的?爸爸杜豐于只能到漫畫出租店租盜版漫畫給他女兒看。
台灣漫畫家邱錫勳就曾經因為在漫畫裡畫了一隻會說話的小狗,而被中華民國當局判定「這小孩子看了會得神經病」的理由而遭到禁刊。這種愚蠢的中華黨國審查制度也導致一堆台灣漫畫家乾脆棄筆不畫改行或是只好跑去日本做代工,重重打擊了台灣漫畫產業的發展契機,也扼殺了民眾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所以在中華民國的戒嚴時代,你根本就不會看到任何台灣本土神怪的創作繪本或是漫畫,你就別妄想當時的台灣會出現像是水木茂或葛飾北齋這類的大師。
—————-
六、無花無愛,只有吳鳳。
你可以在「花與愛」的繪本中看到融合台灣各族原住民的服飾與紋樣,且展現出原民自信與冒險精神。但是很抱歉,當時中華民國的黨國教育其實是以汙名化以及「教化次等蠻夷」的方式來看待台灣原住民的,所以不大可能出現像「花與愛」這種把原住民當冒險主角的繪本。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你在戒嚴時代唯一能看到關於原住民題材的官方核准繪本就是「吳鳳」的故事。故事講述漢人吳鳳在清帝國時期擔任嘉義縣漢番通事,為了遏止鄒族獵人頭的「野蠻風俗」,便向鄒族約定日期與地點,說明當天會有一位穿紅袍且騎白馬的人經過某處,族人即可射殺該人並獵取人頭。結果族人依吳鳳所言射殺該名紅袍者,卻發現竟是吳鳳本人,因此悲痛悔悟,從此棄絕獵人頭的習俗。
這個唬爛故事看似悲壯,但是在原住民的口述歷史中,吳鳳卻是個愛占原住民便宜的漢人奸商,所以最後才會被鄒族出草。然而中華民國不但延續日本時代的吳鳳神話,還將吳鳳列入義務教育的國小課本教材當中,甚至在嘉義車站前樹立吳鳳銅像。這尊狗屁銅像最後也在一九八八年被林宗正牧師、鄒族青年、布農族青年還有民進黨員聯手拆掉,李登輝主政下的國民黨政府隨後也才把嘉義縣吳鳳鄉改名為阿里山鄉。
在「還願」的遊戲當中,杜美心想要跟拔拔一起去「阿里山一日遊」(1985年8月23日),卻因為颱風無法成行。(當時真的有一個結構完整的中度颱風「尼爾森」直接穿過台灣的北部,「尼爾森」颱風屬於容易引發海水倒灌與災禍的「西北颱」,又稱「穿心颱」。)諷刺的是,阿里山的行政區在當時仍然被稱作是「吳鳳鄉」,居住在阿里山的鄒族人仍然被中華民國人視為砍人頭的野蠻民族。
我認識一個曾在大學念過社會系的同學,他的論文就是專門在寫台灣原住民對自我母語的羞恥與排斥感。國民黨以國家式的集體義務教育來汙名化原住民的方式也導致許多台灣原住民產生嚴重的自卑感,甚至不敢在公共場所講自己的母語,也造成一整個世代的原住民與平地漢人之間的互相敵視。你現在還可以聽到一堆中老年韓粉在那裏滿口「山地人山地人」地叫,就是當年黨國教育殘留的遺毒。
—————-
七、杜豐于就是魯蛇版的劉家昌
杜美心的爸爸杜豐于被設定是黨國戒嚴時代的電視劇作家。在中華黨國戒嚴時代,能夠成為知名劇作家或是演藝人員的大多得有「高級四九人」的身分或是親屬血緣關係,而且靠山最好也得是個什麼黃埔將官、蔣家御用走狗或是公立大學教授之類的。像陶大偉的爸爸陶一珊,就是黃埔六期的台灣省警務處處長,張琍敏的爸爸張振國就是中華民國的陸軍少將。
單看「還願」的故事背景,只能透過姓名與口音得知杜豐于一家,包括他的太太鞏莉芳都是所謂的「外省血統」(四九中國人)。但是鞏莉芳後面的靠山是什麼則不得而知,所以她才可以一直跟娘家拿錢還可以拋售家宅補貼家用(鞏莉芳應該不會有祖宅),就算重返演藝圈也一樣有人罩她,不過杜豐于肯定是沒什麼靠山,所以最後才會淪落成這幅淒慘模樣。
從杜豐于書桌上堆疊的書,像是瀛寰搜奇一類的書籍就知道他雖然很愛看書,但是看的好像都不是什麼有營養的書,然後牆上還貼了陸心精神小語與上師慧語錄,這也說明了缺乏才華與智慧的杜豐于只能在中華黨國的庇佑體系下,才能夠在封閉的老三台靠著寫一些爛劇本來生存。然後在缺乏科學啟蒙與邏輯思辨訓練又崇拜獨裁偉人的華文化薰陶之下就註定會變成被「何老師」牽著鼻子走的盲信者。
當民主化的浪潮襲來與社會逐漸開放之後,少了黨國體制的庇護,杜豐于寫的爛劇本根本沒有人想看,也被一堆導演退回,所以鞏莉芳才會罵杜豐于寫的老套劇本已經沒有人想要拍,鞏只好自己再跳入演藝圈來賺家用費。
杜豐于就像是魯蛇版的劉家昌,沒有美國護照版的劉家昌。在失去舞台與鎂光燈的關注之後,就變成一個脾氣暴躁還死要面子的老頭子,整天跟妻子吵架鬧情緒,把所有希望都放在自己子女的星途順利之上,最終導致家庭失和,連子女也被一起捲進來。
杜劉兩者的差別只在於杜豐于是個沒錢的潦倒作家,而劉家昌在戒嚴時代靠著黨國庇護關係所累積的億萬財富依舊可供他三代不愁吃穿。所以這群被黨國庇護的中華巨嬰其實並不是真的那麼熱愛中華民國,他們愛的只是靠著黨國體制所能得到的特權與輕鬆快錢,或是至少能夠輕賤台灣人的「高上位階」。
—————-
八、梅花、鬱金、野百合
一般玩家在「還願」遊戲中通常只會注意到兩種花,一種是梅花(梅花梅花幾月開),另外一種則是杜美心的象徵物:黃色鬱金香(花語象徵沒有希望的愛情)。
但是在遊戲末尾,當杜豐于打開最終的浴室門後,遊戲開始播放「草東沒有派對」的ED主題曲之時,那段充滿亮光的天堂路上除了隨著杜美心足跡而綻放的鬱金香之外,還有另外一種不容易被注意到且稀有的花就叫作「台灣百合」(當ED主題曲的第一句歌詞「只夢到這裡…」出來的時候,台灣百合就出現在左邊的風車旁,然後鏡頭很快地就帶過去)。
台灣百合(Lilium Formosanum)除了是台灣的原生特有種之外,也一直在台灣民主的歷史上佔有重要的象徵地位。由於台灣百合可以在冬季冷風肆虐下與惡劣如陡峭懸崖邊的環境下生長,除了被魯凱族當成崇高的榮耀之外,也被認同台灣的人視之為台灣國花。
對於熟悉台灣民主歷史的人而言,「野百合學運」更被視為是一個重要的標記點。八○年代末期,也就是杜美心或杜豐于即將面臨死亡關頭之際,台灣社會開始了要求政治改革的浪潮。而首波被要求改革的對象就是多年未改選的萬年中國民代(民間稱為老賊)。
一九九○年三月十三日,多年未改選的國大代表在陽明山中山樓通過修正案,自行通過法條將自己的任期延長。這種無恥的自肥擴權行為也迅速引發社會與學生團體的反彈。
三月十六日,數十名台大學生與工技學院的學生自行前往臭頭廟靜坐,拉起「同胞們,我們怎能再忍受七百個皇帝壓榨」的抗議布條,也開啟了學運的序章。在短短數天之內,原來數十人的靜坐擴大成數萬人聚集的全國學運。
台灣野百合也因此被選為運動的主視覺象徵物。隨後國民黨籍的總統李登輝也回應了部分學運人士的訴求,包括召開國是會議與修憲,立法院與大法官會議則協助完成終結萬年民代。野百合學運可說起了關鍵的作用。至今台灣政壇上仍可見到許多野百合世代的主要參與者在活躍。
梅花、鬱金香與野百合就像是台灣民主歷史上的三種人,梅花是殘抱著黨國體制的中華大一統主義者,鬱金香則像是在台灣民主歷程中不幸受難的無數前輩與平民,而野百合就像是新生的台灣認同世代,繼承上一代人未竟的建國工程與獨立意志。(遊戲中還有一種台灣路邊常見的「長春花」,又名日日春或五瓣梅,出現在杜美心以嬰兒抓周狀態爬上舞台時的場邊裝飾。)
這三種花在遊戲「還願」中分別以不同的意象出現。梅花首先出現在杜豐于的最佳編劇獎盃上,然後又以黑暗的紙紮人形一邊轉著車輪盤座,模擬霍納 (William George Horner)所發明的西洋鏡(zoetrope)連續動畫效果,然後一邊說著「梅花梅花幾月開」的恐怖方式出現;鬱金香則是以帶著溫暖卻悲傷的方式出現在遊戲的各個角落;而台灣百合則是在遊戲的最末尾結束之處以救贖與光明的隱晦方式伴隨著鬱金香一起出現。不過後來的「習近平小熊維尼你媽八七」事件可說搶盡了「台灣百合」的鋒頭,所以幾乎沒有人發現到如台灣獨立象徵物一般的野百合在劇末的存在。
最後我想說的是,杜美心唱的「碼頭姑娘」這條歌,其實跟「何日君再來」與「長崎蝴蝶姑娘」一樣,你可以把它們當成一般的情歌,也可以用後殖的角度來解讀那種被殖民者期待「祖國」重返的心態。赤燭嘗試用當時戒嚴時期的華語風格去「復刻」這首歌曲,不懂當時台灣時空環境的中國市場說不定還會因此誤讀成「現在的灣灣期待回歸祖國」,對「還願」團隊可說是心機梗或是兩面光。當然,小熊維尼事件爆發後也就沒什麼好說了。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想像在「還願」所處在的80年代,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台灣人還真的以為自己是中國人。若是當時蔣經國沒有及早暴斃,拖到90年代,國民黨這群老宮廷派加上掌有軍權的郝柏村真的可能會在全台灣有九成以上的人自認為中國人的「民意」之下,在六四事件的輿論平息之後,以經濟會談的名義與中國展開統一和談,後面哪裡還會出現「國際橋牌社」的劇情,這比「還願」還恐怖多了。蔣經國的七孔流血暴斃可說是台灣的萬幸。
不過三十多年前,台灣這塊曾經長滿「梅花」的土壤最後卻長出了「野百合」,可說是意外,是運氣,也是奇蹟。
(謝謝你看完這篇連我自己打完都覺得很長的文。)
RELATED POSTS
View all
